2024年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适逢戴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推出系列纪念文章,怀念这位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

2024年1月24日,一个哀伤的日子。上午,有事与国内联系,未料竟听到恩师戴逸先生于当日早晨离世的噩耗。消息如晴天霹雳炸在头顶,我身体发僵,脑里一片空白。稍缓过神,想到从此再无缘得见先生的音容,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隔海遥拜,哀思绵绵……
我于1985年硕士毕业后进入清史研究所任教,同年考取戴逸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我的上一届师姐师兄是黄爱平和朱雍两位,他们也是戴师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的首届博士研究生,下一届是师弟杨念群。虽然入师门在1985年,但因父辈的渊源,戴师很早就是我熟悉的儒雅可亲的长辈。20世纪40年代后期,父亲在北大史学系与戴师同窗,田余庆先生是他们的高年级学长。母亲读化学系,与戴师同届当选校学生会理事。他们一起参加进步社团活动,投身学生运动,后来都奔赴了华北解放区。老一辈人的笃厚情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的晚年,在送给父母的书上,戴师仍用他在北大时的旧名——戴秉衡。父亲后来未能从事史学领域相关的工作,这是他的人生遗憾,但他十分敬重戴师的学问成就。我1978年考入人大历史系本科后,父亲一再嘱咐我好好读戴师的书,用心求学。我有幸在《简明清史》(上册)刚刚出版的1980年就得到戴师亲笔签名的赠书,这也是我的第一本戴师赠书(此后先生每有新著,都会赠我一册)。四十多年过去,书页已经变脆发黄,我一直带在手边,无比珍惜。那一年我刚上大三,对清史的了解尚浅,而书中展现的清史脉络、戴师对历史的高度驾驭以及优雅畅达的文字都深深地吸引了我。可以说,《简明清史》是引导我走向清史专业的第一本书。
我进所不久,恰逢“清代边疆开发研究”课题组成立。该课题是国家“七五”计划社科基金项目,由戴师领衔、马汝珩老师具体主持,我和本所许多同辈人如成崇德、何瑜、潘向明等也都有幸参与其中。戴师说促使他加意关注清代边疆史这一领域的契机是珍宝岛事件后应中国外交部的要求,研究并撰写《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人民出版社1977版),历时四年通过大量搜集当时可见的中外一手资料,将考史与释史相结合,第一次翔实地阐释了该条约问世的过程,也充分感受到边疆研究的重要性。关于当前课题的意义,戴师强调,历史科学应该迈开坚定的步伐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清代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最为密切,只有研究清代和近代边疆开发的情况,才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的基础和过程,更深刻地认识边疆的现状。[1]
对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和课题组内的分工,戴师建议可着重研究新疆地区,因为和其他边疆地区相比,清朝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开发着力尤多,内容丰富,而目前研究尚少,亟待开拓。他还指出,中国今后必然要加强对边疆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开发,研究清代新疆开发史,对当代的西部建设将有重要借鉴意义。时光流转,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政府正式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戴师的预见高屋建瓴,不仅为当时的我指明了研究方向,更充分显示出他作为当代史学大家不凡的前瞻眼光,也体现了先生践行一生的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秀学风。我曾下乡插队,在内蒙古草原上度过了八个年头,这段经历让我对边疆的民族、人文、历史本能地怀有很深的关切,先生的建议既针对了我的这一特点,又考虑到清代边疆开发史研究的现状。感谢先生的指引,从那时起至今日,我在学术上与新疆结缘已历四十载,缘深情笃,将继续在这片天地里努力耕耘。
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后,先生对我的另一项要求是在史料上下足功夫。他说,时至今日要做好清史的学问,绝不能止步于已有的历史文献,必须向档案中求史料,才可能深入和出新,做清代新疆开发史,尤其应当如此。于是,到档案馆去,搜集第一手史料,成了我的行动指南。我是在职读博,日常的教学等工作甚多,须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一连数年,我骑车奔波于西郊人大和西华门之间,风雨无阻,未曾间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年的阅档条件很简陋,一间大屋,几排长桌,冬冷夏热,没有电脑,更没有数据库可用,一切全凭手抄,目录也很不完备。但有一点是今天的阅档人无法企及的,那就是我们可以亲手触摸和翻阅档案原件,置于面前,逐字细读,沉浸在档案带来的历史氛围(连同原件的纸屑和灰尘)中。四十年过去了,我坚持奉行“向档案求据,让历史鲜活”的初心,注重对档案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也可以说是个人的研究风格。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订,以《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为书名出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8年再版)。先生为拙著作序,称“此书对清中叶以至清末新疆的开发与经营进行了研究,叙述详明”,作者“勤奋努力,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故使此书达到了较高水平”。[2]先生的肯定是对我最大的鼓舞。
与此同时,先生也鼓励我多走出去实地踏查。1986年我和戴师一起参加在伊宁市举办的“林则徐遣戍新疆145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会议的论文,通过深入挖掘档案史料,第一次厘清了林则徐南疆勘垦的全过程。戴师在大会上发言,又应《新疆社会科学》编辑部的请求撰写《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一文,发表于该刊1986年第5期,在新疆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会后代表们前往伊宁县巴依托海村老龙口旧址考察,这项水利工程正是流放此地的林则徐亲自主持修成的。在老龙口前,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样的实地考察很有意义,对你很重要,要多争取这样的机会!”多年后,戴师在《光明日报》发表《林则徐与近代新疆开发》一文,再次高度肯定林则徐在伊犁兴修水利以及从事南疆勘垦的历史功绩。而我,迄今已十次来到新疆,考察的足迹基本覆盖了天山南北各地,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对新疆人文历史的感知。其中2007年两度重到伊宁,每次旧地重游,都让我想起1986年与戴师同来时的情景,忍不住感慨万千。
1992年,戴师的又一部清史研究代表作《乾隆帝及其时代》出版。恰如书名和前言所示,这不单是帝王个人的传记,而是将乾隆帝及其所处的18世纪同时纳入考察范围,由人物而及时代,由中国而及世界,以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和把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宏阔视野和学术气魄。在此基础上,戴师进一步形成了将18世纪的中国置于世界史的坐标之上做“全景式”考察的设想,这一设想的落地,就是国家“八五”计划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该课题的申请筹备从1990年末即开始,至1992年确定立项,课题全面展开。其时我正在所里任副所长(1989—1993),主要负责科研和外事方面,因此有机会较多地参与了这项工作。戴师对课题论证要求很高,申报材料数易其稿,反复打磨,对团队的组成也是斟酌再三。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无二的学习经历,使我有机会近在先生身旁,时时倾听他的深刻思考,努力领悟;有时也参与讨论,发表些不成熟的意见,得到先生宽宏的鼓励和采纳。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课题获得6万元的国家经费支持。若放到今天,这个数目完全不足道,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应该是社科基金历史学类项目能拿到的最高等级了。
按照戴师制定的研究框架,本课题由导论(戴师执笔)及多卷本分论组成,其中政治卷——郭成康,经济卷——陈桦,社会卷——秦宝琦(后张研亦加入),边疆民族卷——华立(后由成崇德接手),文化思想卷——黄爱平,对外关系卷——吴建雍,后来增加了军事卷——戴逸、张世明,以及农民卷——徐浩。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初是撰写研究提纲的第一阶段,为了更好地发挥团队研究的优势,课题组采取了分次研讨、修改完善的形式。每次由某分卷负责人报告所拟提纲,戴师讲评,再由团队成员各抒己见,每个单元用时半天,视情况多次进行。戴师的讲评并非居高临下式的指教,而是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将多年积累的研究所得和思考娓娓道出,与我们分享。在场的所有人都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和热烈。这样的研讨形式当时在清史所内不多见,系借鉴吸取了日本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常见的研究班方式。1983年戴师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之邀访日时,曾参加狭间教授主持的“辛亥革命研究”项目,多次在研究班上为日本学者讲析中国近代文献资料,对这一方式甚予好评。前不久我在北京家中整理旧物,发现竟然还保存着几盒当年的录音磁带。我如获珍宝地将盒带放入录音机里,当听到戴师及团队同仁们熟悉的声音,顿如从时光隧道穿越回30多年前的研讨会场,又坐在了先生身旁,一时百感交集,不能自已!经过半年的研讨,1993年《清史研究》第1期特辟“笔谈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专栏,戴师以下计12人执笔(我为其一),可视作提纲研讨的阶段性成果。这之后,我因为赴日本任教的关系不得不离开课题组,未能与课题同始终,我心中有抹不去的遗憾和歉意。可喜的是,经过多年努力,煌煌巨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九卷本于1999年由辽海出版社刊行。戴师的《导言卷》提纲挈领,指出“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贯串在18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主题就是近代化问题”“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才能认识中国的真实地位和状态”。[3]这一前所未见的崭新尝试也得到西方历史学界的认可,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Jochen Schlobach)亲自撰写序言祝贺九卷本的出版,称“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4]。
1988年至1992年,戴师连任中国史学会第四届、第五届会长。算上此前担任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主席团成员等,其在中国史学会任核心职务达十数年之久。作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胸怀全局,洞察潮流,充分发挥中国史学会引领学术风气、推动史学不断发展的作用。我至今记得,1990年正值鸦片战争150周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否定鸦片战争中抵抗派的意义、美化殖民主义者等错误认识,戴师要求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不仅中国史学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学术研讨会,戴师还提议人大也组织召开学术座谈会,由清史所和历史系联手,以“鸦片战争以来爱国主义的发扬”和“近代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作为主题,邀请在京各史学单位参加。其间戴师和李文海老师多次召集我们开会,仔细询问如何邀请近代史名家,是否有专人对接,如何发布消息,宣传是否到位,等等,甚至连能否安排午餐(当时系所经费紧张)这样的细节都过问到了。由于准备充分,原来预计与会30至50人,实际超过了60人,会议开得热烈而深入,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更让我难忘的另一件事情是,在戴师倡议下,由中国史学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于1991年在西安盛大举行。戴师的“爱才”“惜才”是出了名的。他常说青年人是史学发展的希望,不论何人,不论是否门生弟子,只要有心向学,他都亲切接纳,谆谆教诲,全力提携。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力排众议将历史小说作家曾黎力(凌力)调入清史所,以及近年安排历史文学作家张宏杰入所,都是非常经典的事例。主持中国史学会后,他更是把关心、培养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与一般的学术会议不同,“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的参加者系从全国选拔,专业覆盖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及世界史等众多学科领域,需要先经各省社科院历史所和全国各高校历史系分别推荐,提供相关材料,再由组委会核准。相对于庞大的史学队伍,会议名额有限,既要推选优秀人才,又要合理平衡,在政策上的分寸拿捏也很讲究。而且,在一切联络都依靠书信往返的时代,筹备事务极其繁缛。戴师决定依托人大来处理具体杂事,由我、徐兆仁(人大历史系)、赵世瑜(北师大历史系)、高毅(北大历史系)组成一个小组,我任组长,国家教委派一名同志坐镇,人大历史系王汝丰老师是史学会副秘书长、会议组委会成员,也是我们的直接领导。那几个月称得上是高强度运转,加班加点,好在小组成员齐心协力,保障了筹备的进度,我们每个人也都得到了历练。在西安会上,我们几人既是代表,又兼任会务组。近百人的参会规模,单是每人带来的打印论文,就在房间里堆得如小山一般,整理和分发材料的忙乱程度可想而知。其他代表看到此情形,也纷纷加入帮忙,笑称年轻人帮年轻人,不分彼此。会后以“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为题出版了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书名恰如其分地点出了会议特色之所在。现在回想起来,这次会议确实堪称史学界青年一代的“群英会”,与会代表后来几乎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一方诸侯”、领军人物,至今活跃于海内外的史学舞台。“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迄今已召开了七届,优良传统得以承续,而先生的首倡之功,尤不能忘!
1993年以后,我居东瀛,见先生的机会少了。幸运的是,1995年和1997年,戴师又两次访日,使我有机会在海外随侍左右。1995年值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一百周年,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在东京举办“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国际研讨会,戴师应邀到会并做“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形势”的学术报告。我也从大阪赴会,与先生小聚并充任翻译。在此之前,戴师出版了新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将这场影响了中日两国乃至近代东亚命运的战争置于世界格局中加以考察和阐释,作为展现中国学者历史认识的力作,在日本受到关注。先生在会上的报告即凝缩了书中的核心思想。数年后,在我和另外两位译者的努力之下,本书的日译本《日清戦争と東アジアの政治》(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部2003年版)面世,能为弘扬先生的学术思想尽力,令我深感欣慰,当然这是后话。
1997年戴师再度访日,这次的行程较为宽松,大阪—下关—东京,历时一周,我全程陪同。今天的下关即近代史上的马关,该行程系东道主一桥大学的江夏由树教授根据戴师的愿望特意安排。戴师多次讲过他的治学乃循“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远而近,由今至古”,从而做到前后贯通、古今贯通,这一点成为戴师治史的突出特色。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甲午战争及其代表人物李鸿章是他长期关注的一大重点,这次亲到当年的马关踏访,了却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下关的春帆楼宾馆院内建有日清议和纪念馆,馆内复制了当年的谈判现场(原址在该宾馆二楼),还展出大量有关文物。当时有一个小插曲:展品中有几幅李鸿章的墨宝引起先生的格外注意。原来他正在主持《李鸿章全集》的整理和编辑,而这里的几幅中,有之前在国内未曾见过的,因此要我一一拍照,给他带回去研究。我立即遵办,但是玻璃框的反光过强,无法拍摄清楚。陪同我们的下关市立大学金子肇教授见状,便与该馆负责人协商,那位负责人当即表示理解,将原件从框中取出,请戴师仔细阅鉴。离开春帆楼后,我们一行又先后到访了李鸿章曾下榻的引接寺和山口县公文馆等处。到达东京后,戴师在一桥大学做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专题演讲,圆满结束此行。至于体量巨大的《李鸿章全集》,则历时十数年而告竣,全39册,计2800余万字,于2008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多年后戴师再谈到那年在当地受到的友好接待,又一次表达了感谢之意。还要提及的是,在下关与戴师同行的日本学者里,包括了神田信夫、松村润、细谷良夫等多位日本清史学界和满学研究的顶级学术大家,他们都是戴师的老朋友,一路相谈甚欢。而跟随身边的我,对于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除了惊喜和兴奋其实还有少许忐忑,毕竟这个阵容实在是太过“豪华”了!
这些年来,每次从日本回到北京,我都会去看望戴师,每看望必长聊。聊天的内容天南海北,很随意。先生询问我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叮嘱我不可放松研究,也问及日本的学术动向,有时则将正在思考的一些学术问题拿来与我探讨和分享,还会讲一些远年的家乡旧事,特别是熏陶启迪了少年戴逸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那份浓郁的乡梓情怀,感人至深。渐渐地,这看望成了师生间的一种习惯。有时我回京后杂事多拖延了几日,先生会叫人来催。一次师妹赵珍发微信给我,半开玩笑地说:“老师想了,你快去吧!”
2002年,戴师受命出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清史编纂工程。编修一部接续《二十四史》的新型正史《清史》,是先生一生孜孜以求的最高学术梦想,现在终于有了施展抱负的宏大舞台!这一年,先生76岁。先生说:“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从受命之日起,先生的所思所想,只有“清史”二字,此后与先生的长聊,自然也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先生为我讲解这次纂修清史的整体构想,说明兼取纪传体和编年体之长创设“五位一体”(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的“新综合体”的必要,还强调修史须与史料的发掘整理并行。通过一次次交谈,我分享了清史工程的点滴进展带给先生的欣喜,也体会到其中的曲折艰辛与先生的操劳。每次去铁一号的西小院,总看到先生的案头堆满了要审阅的清史稿件,摊开的那几本,字里行间写满先生的批语。为了加快清史编修的进程,早日完成国家的托付,先生夜以继日,奋力改稿,毫无休息,完全忘了自己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那情景,让我心疼,更肃然起敬!我因人在国外,未能直接参与清史工程的工作,不能替先生分忧些许,时感自责。2015年,清史编委会邀请我担任卜键教授主持的《边政志》卷的主审专家。那时我身体有恙,健康状况较差,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经过数月的认真审读,写出了详尽的审稿意见,如期完成任务。当我向先生汇报此事,他连连点头说:“好!好!”
2006年值先生八十寿诞,我和何瑜等几位同门曾有编辑一本贺寿文集的想法,没想到一开口就遭到先生坚决反对,说:“现在正全力推进清史工程,事业任重,大功未成,何来庆贺?免谈!”不得已放弃此念,仅由何瑜代表同门敬献木雕老人表达心意。到了2015年,先生的九十寿诞将至,我和诸同门又一次萌生了编辑学术论文集以为贺寿之礼的想法。是年2月回京时,我去探望先生并恳切地表达了大家的愿望,这次先生勉为应允,但提出注意事项,告诫:“务必低调,不得大张旗鼓,为人行事要谦恭检点。”见先生终于点头,我太高兴了!自此,贺寿纪念文集提上日程。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感谢师弟杨念群的倾力操持,从征稿、编辑到出版,花费巨大心力,完成重任,将《澹澹清川:戴逸先生九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作为及门弟子和清史所同人的九十寿礼,奉献于先生面前。我在海外,未能更多出力,仅提交了一篇2万余字的论文。先生寿诞的九月,清史所举办了“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我在照片上看到先生的满面笑颜。我相信,这是他最开心的生日之一,而《澹澹清川》无疑是先生最珍视的、格外具有意义的一份庆生贺礼。
最后一次面谒先生是2022年3月。自2020年疫情以来,交通阻隔,回国不便,直到下决心历经种种隔离回到北京,才有了探望先生的机会。当时北京仍处在严密戒备疫情的态势下,从先生的健康出发,应否前往,我心存犹豫,于是先征询戴寅的意见。他很快回复:“来吧,老爷子想见你呢。”时隔两年多再见,先生的气色不错,笑意盈盈,唯听力较前又下降不少,腿力也不如前了,有时要附在耳边大声说话,有时索性用笔谈。我呈上自己的新书《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先生一边翻看,一边微微颔首,戴寅和戴珂也同座叙谈。在此之前我已听说《清史》的送审稿不如预期顺利,为不引起先生更多焦虑,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方面的话题。不知不觉,近一小时过去,我和丈夫起身告辞,先生目送我们离开。我走到院子里回身向他挥手说:“明年还会回来看您的!”谁曾料到,这个承诺再也无法兑现,那一日的告别竟成了我与先生的永诀!
2024年1月30日告别仪式当天,我隔海与先生作别,一幕幕往事伴着泪水在心头翻滚。
先生走了!告别仪式上的巨幅挽联——“三百年清史垂鉴笔削有法真司马,七十载教泽绵延俯仰无愧大先生”——极写戴师一生,字字精当,恰如其分。“真司马”“大先生”之誉,先生当之无愧。
先生走了!在家人的护送下,归葬他深爱的故土——常熟,在美丽的虞山脚下与师母团聚,从此安眠。先生的高尚风范和卓越成就,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弟子,唯有秉承先生教诲,在他指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奋力不怠。与此同时,我也由衷地热切期望,浸润着先生心血的《清史》早日完竣,付梓行世,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简介:华立,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名誉教授。文章刊于《东吴学术》2025年第一期。】
注释:
[1]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第6-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戴逸:《序言》,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第3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3]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第1-6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4][德]约翰·施洛巴赫:《序言》,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第1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转载请注明来自亚星官方网-亚星开户-亚星代理,本文标题:《戴逸逝世一周年丨华立:回忆在恩师戴逸先生身边二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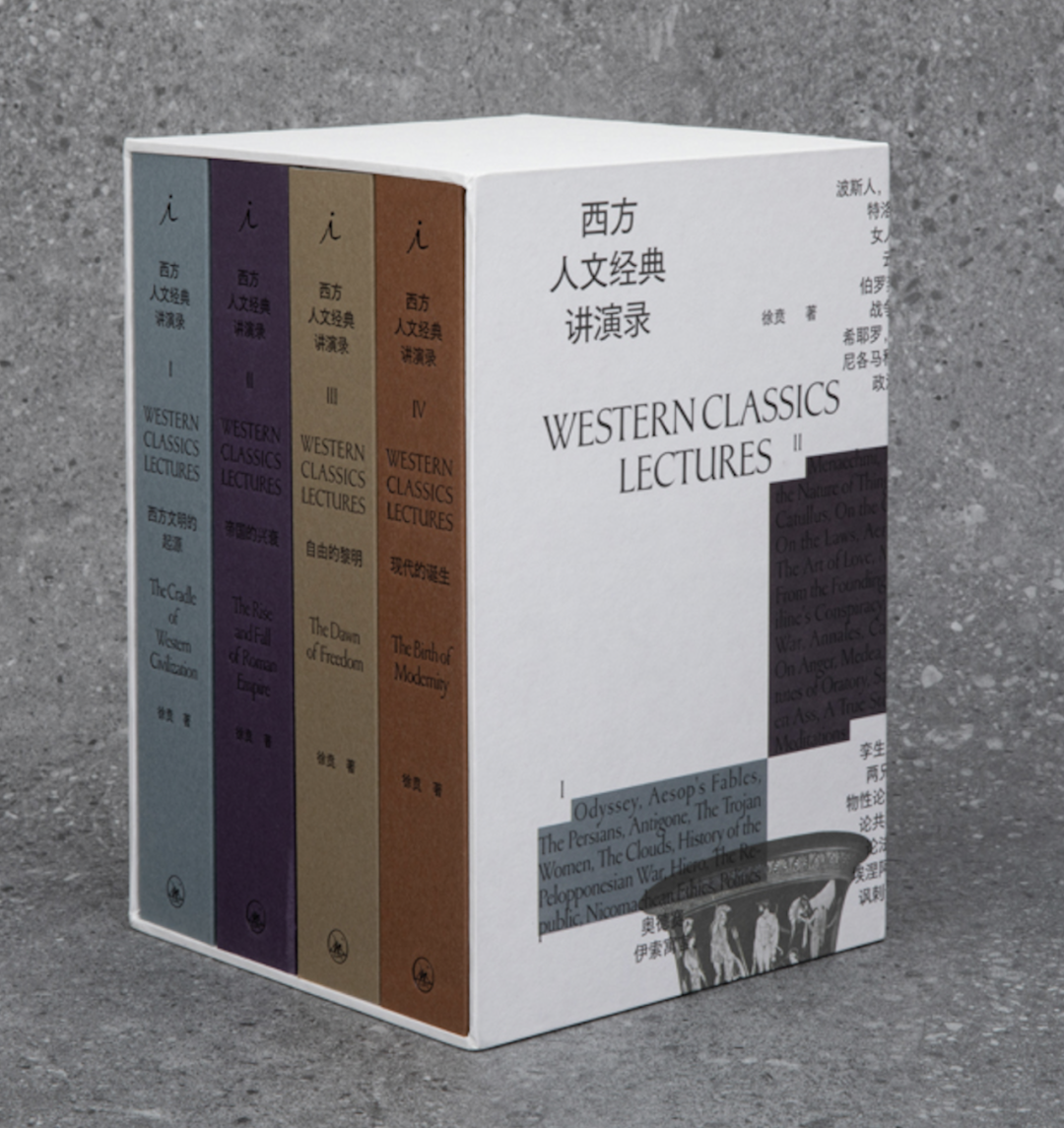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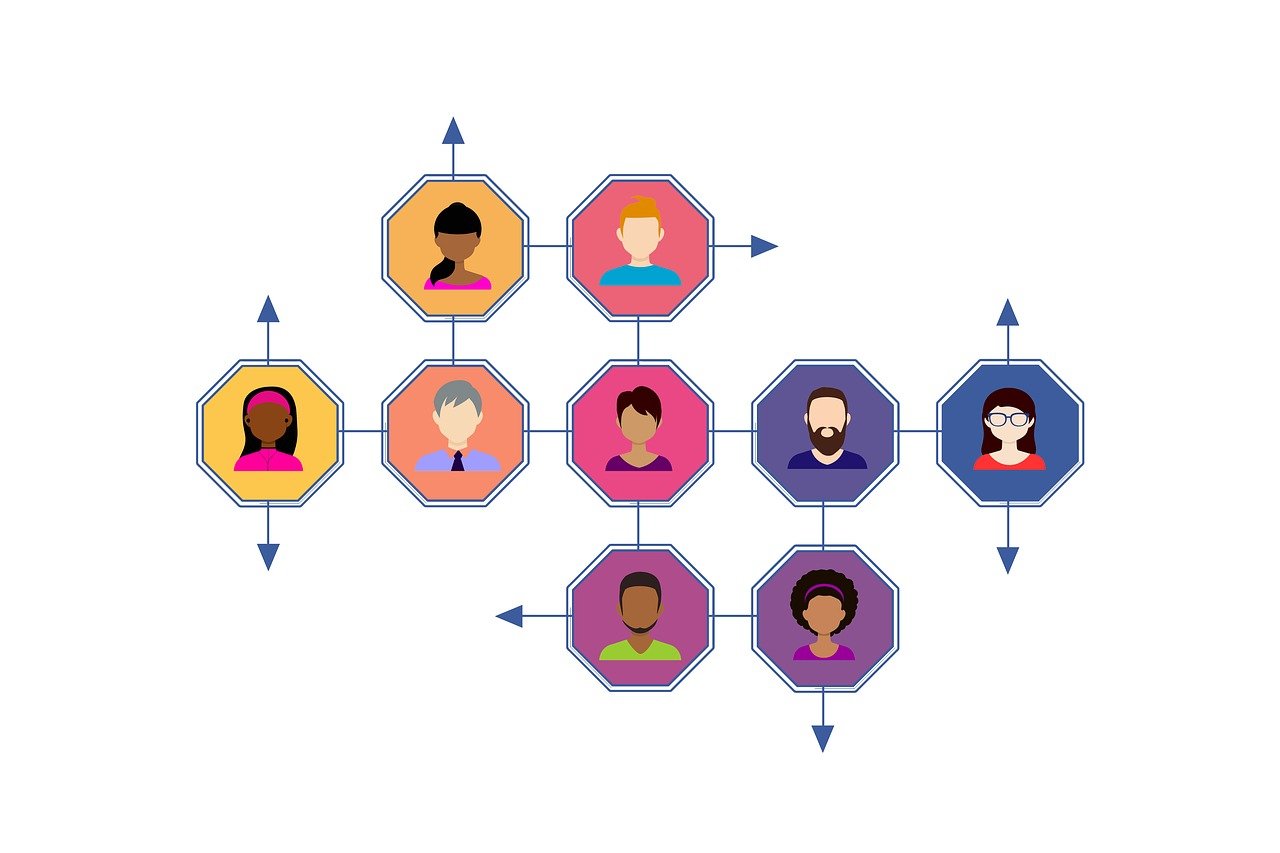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