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过去大半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图书馆。除了周一上午闭馆,这里几乎可以收容我在睡觉之外的所有闲暇,是名副其实的“公共空间”。
我在这里遇到很多人。有个面目潦草的流浪汉,就连炎夏也穿着包浆的长款厚大衣,拎着大包小包,但从不打扰他人,找个座位坐一两个小时就走。一个穿得光怪陆离的男子,日复一日摇着扇子在室内室外不停走动。还有一对情侣,似乎刚进入热恋,桌上摆得像个零食小卖部,他俩躲在零食堆后窃窃私语,夹杂着拥吻。
我承认自己的神经相当敏感,才会对这些小动静尽收眼底。但我也知道,一个在公共空间里的人,要有能力面对各种白噪音。
我的情绪具体是在哪天被引爆的,已经不记得了。总之那天有突兀的手机提示音响起,它不同于那些白噪音,显得强势,穿透力十足,且一声接一声。陆续有人抬起头来,朝着声音源深深叹气。这场景迅速刺激得我的火气像河豚般鼓胀起来。我半个字都没办法再看下去,试图劝住自己:“深呼吸!不要发火!不要跟素质低下的人一般见……”但我的嘴已不听使唤地怒喊出来:“能不能把声音调小点,这里是公共区域!”
那一瞬间,整个自习室都安静了,旁人纷纷转头朝我看过来。我还停留在“嘴怎么不听劝”的惊愕中。等缓过神来,又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响起,像当众给了我一记耳光。我赶紧给自己喂了颗麝香保心丸。
被引爆的情绪是很难收回来的。从那天开始,我逐渐养成了在图书馆里维持安静秩序的习惯,频繁提醒人小点声、别公放、出去打电话。那些被提醒的人,脸上常常浮起讶异,好像首次知道这个规则似的。但绝大数情况下,我的提醒是奏效的。
有次我对面坐着个胖爷叔,也是手机提示音连环响。我说,能麻烦您调成静音吗?他说,好。过了会儿,另一串连环提示音响起,我冲着空气怒喊:“能不能把声音调小点,这里是公共区域!”爷叔特别惊惶地看着我:“不是我……”我气急败坏地说:“没说您……”
不得不说,这是个令人感到挫败的瞬间。被提醒的人已经夹起尾巴,而他背后的暗处,躲着某个看不清面目的挑衅者。维持秩序者的“枪”由此失去准头,实在是沮丧。
久而久之,我发现这间自习室里出现了我的同道者。我们散落在不同的角落,互不相识,又心怀默契,各自对片区内的噪音进行干预。有天,对面片区的某台电脑突然开始大声讲课,电脑的主人不在,一位女士站起来走过去,直接动手掐掉了它的声音。还有一天,几个人合力劝走了一个打视频电话的老外。可以说,只要图书馆开着,我们永远都有得忙活。
老实讲,我很乐于见到越来越多人对公共空间的噪音不再容忍。但另一方面,我又为其中的尺度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手持道德的大棒,挥向谁、用多大的力度,我们不见得能拿捏好。大多数人对噪音没有那么应激,我们这些更敏感、更喜欢出头的人,能代表大部分人的意思吗?平衡点又在哪里呢?
有天跟朋友聊起这件事,她非常诧异我为什么会想这么多。她觉得这件事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公共场合就应该收声。她说去日本旅行,无论是在新干线里还是在咖啡馆,几乎听不到人大声喧哗。举轻以明重,图书馆这种空间,人们更应当自觉保持安静。
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之所以如此警惕,恰恰是因为在图书馆提醒人不要出声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微妙的道德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感到不安,总想掐灭它们。康德曾经说过,为了获得某种满足感和道德优越感的行为,并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再细想下去,我恐怕就要变成这种“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的人。
然而,当我次日再走进图书馆,这种自省就会烟消云散。新一天的噪音又是新鲜的挑衅,只会让我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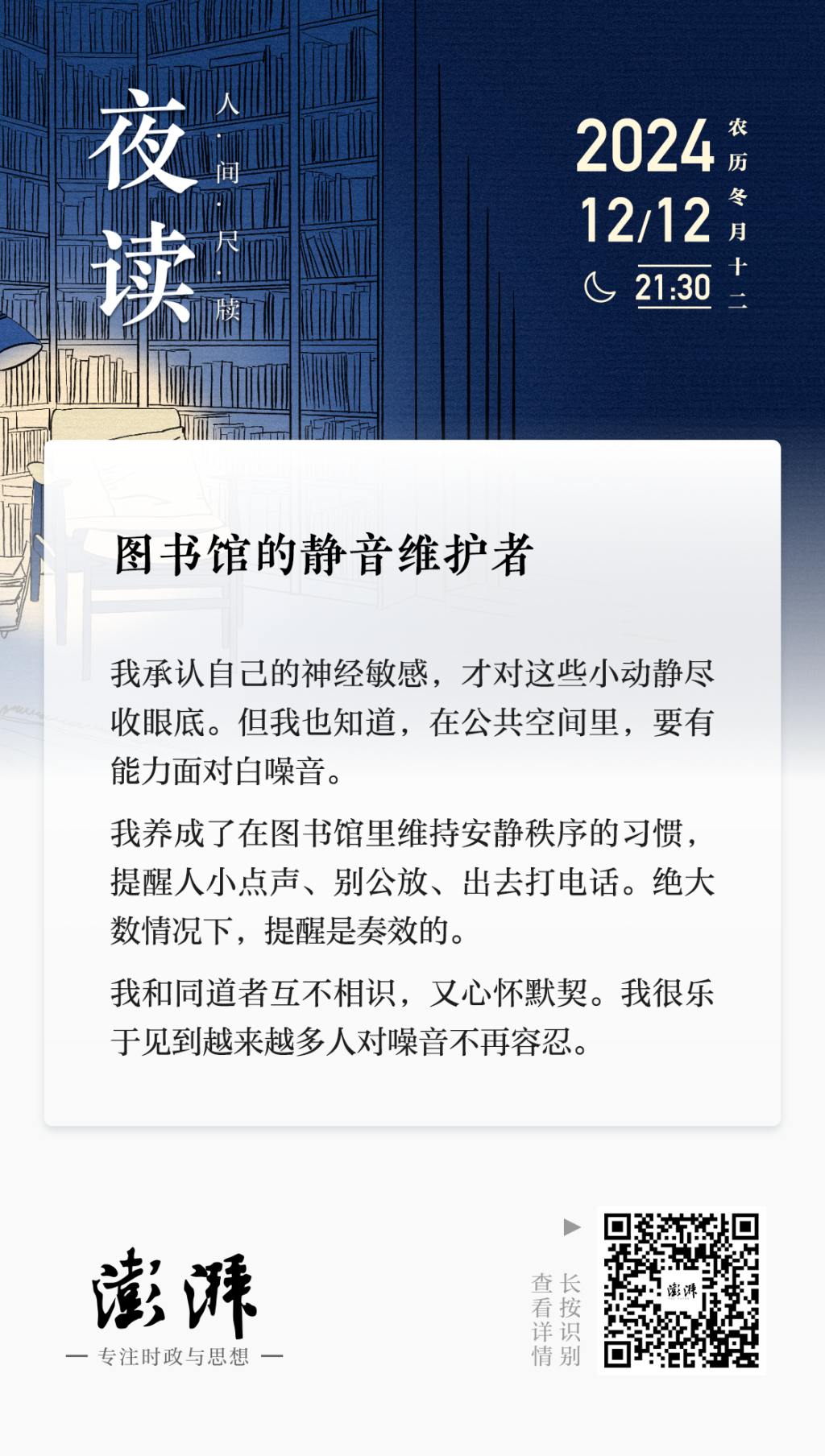
转载请注明来自亚星官方网-亚星开户-亚星代理,本文标题:《夜读丨图书馆的静音维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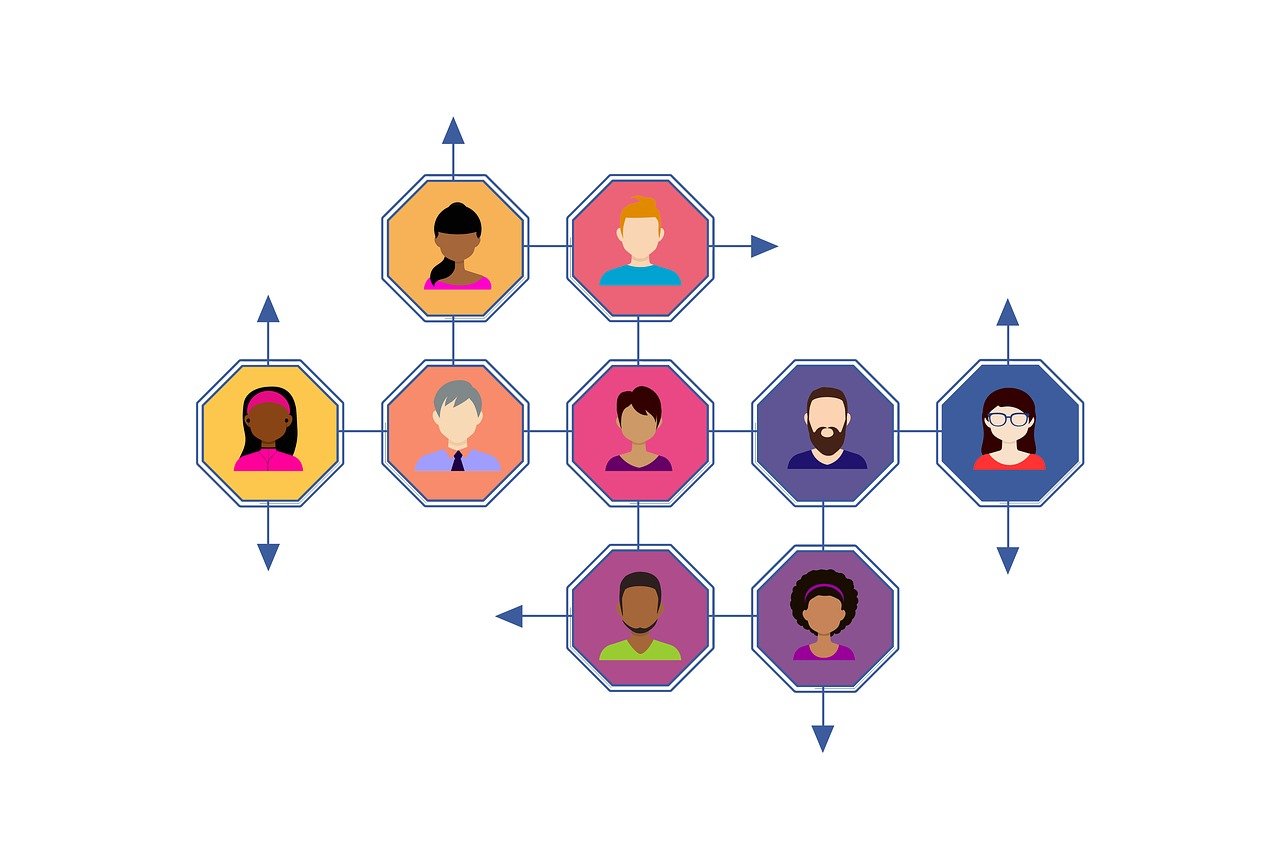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