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来信: 蒙太古夫人书信集》,[英]蒙太古夫人著,冯环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版
1763年,蒙太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年)遗著《东方来信》(The Turkish Embassy Letters)出版,旋即成为畅销书,在英伦和欧陆一版再版。由此,作者本人也像前辈塞维涅夫人一样跻身于欧洲著名书信作家之列——“崇英派”代表人物、同为书信作家的伏尔泰甚至夸赞其文友蒙太古夫人“文笔更胜一筹”。而在十八世纪艺术史家布鲁斯·雷德福(Bruce Redford)教授看来,蒙太古夫人的文笔的确堪与蒙田媲美:其“调性貌似平实,其实极具欺骗性”(in deceptively smooth cadences)。从表面看,《东方来信》不过是一部描绘异域风情的海外游记,但实质上,作者却要借“他国之眼”来展示她的辉格史观(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716年4月,蒙太古夫人的丈夫沃特利被任命为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随同出使。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劝阻英国盟友奥地利卷入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的战争——否则英国独木难支,将无法制衡天主教法国和西班牙在地中海的势力。在一年半左右时间里,蒙太古夫人将沿途所见所闻(尤其是旅居土耳其的感受)详细记录,寄呈国内亲友,如胞妹马尔夫人(其夫马尔伯爵是铁杆保王派,曾发动詹姆斯党人[Jacobites]叛乱)、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威尔士亲王妃卡罗琳、里奇夫人(卡罗琳王妃侍女)和布里斯托尔夫人(英王乔治一世王后夏洛特侍女)等。这五十余封书信,长短不一,话题各异,也无只言片语触及敏感时事(或说蒙太古夫人晚年曾亲手删改)。然而在评论家看来,这正是《东方来信》的高明之处:无论身在何处,尽管不着一字,作者心心念念的仍是故国的政体民情。
身为辉格党元老金斯顿公爵长女,蒙太古夫人早年因与绅商之子沃特利相恋遭家人反对,被迫连夜私奔出逃,闹出惊天丑闻,这也使得她对穆斯林社会的女性地位问题尤为关注。比如在一家土耳其浴室(她戏称该公共场所相当于奥斯曼的伦敦咖啡馆):“浴室里盈满了女人们的喧闹声,有人在梳头,有人在喝咖啡,嬉笑打闹,热闹非凡。她们尽情地享受属于自己的私密天地,完全不受男性的干扰。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的女人拥有如此喧哗的独立空间。”与英国妇女不同的是,穆斯林妇女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撑,奥斯曼妇女不必再像其他地区的闺阁女子那样悉听尊便于丈夫,而是拥有了在家中拍桌子的资格。她们的意见不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须被重视的声音。”
蒙太古夫人在浴室结识了一群穆斯林上层女性友人,与伦敦名媛沙龙漫天的诽谤中伤相比,这些女士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真诚互助令她羡慕不已。这也促使她情不自禁地将两国女性的处境进行了对比:尽管当时的土耳其实行一夫多妻制,但女性由于蒙有面纱的缘故而享有某些自由,那种“遮掩给予了她们随性而为的彻底释放,却丝毫也没有被发现的危险”。相反,英国女性却受到阶级、性别和道德的多重束缚。据蒙太古夫人自述,入浴之际,她出于害羞,不肯解下紧身胸衣,遭到当地妇女耻笑,认为是其丈夫施加的“牢笼”。蒙太古夫人只得自我解嘲,说自己婚后确实成了俘虏,被囚禁在婚姻这一部庞大的“机器”里。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把三种不同类型的婚姻分别比作乐园、地狱和炼狱——自由婚姻是乐园,包办婚姻是地狱,而炼狱则指与一个可以勉强相处的人成婚。在信末,蒙太古夫人感慨系之:“在英格兰,我们的性别遭受如此轻蔑的对待,在这一点上,世界其他地方无法与之相比。我们在粗俗无知中接受教育,所有的技艺都在扼杀我们的自然理性。”
与书信中不经意流露的“性政治”相比,蒙太古夫人对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状况的刻画笔触更为细腻。历经数百年统治,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已呈衰微之势:“该帝国政府现已完全落入军队手中,那号称拥有绝对权力的大君(Grand Signor)竟与他的臣民一样也沦为了奴隶,只要土耳其士兵皱一皱眉头,他就会吓得簌簌发抖。而这里的人们也的确表现出了一种远甚于我们的卑下服从之状。他们面对某位国务大臣,是不能直接与之对话的,得双膝跪地才行……而如果哪家咖啡馆里冒出一句关于大臣如何行事的议论——大臣在各处安插密探——那么这家咖啡馆就会被夷为平地,且馆中的一帮人或许还都会被施以酷刑。”所以,与十八世纪伦敦盛行的“街头政治”相比照——这里“既没有欢呼喝彩的暴民,也没有胡话连篇的小册子,以及酒馆里关于政治的争论……也没有我们那些不痛不痒的谩骂”——在蒙太古夫人这位辉格党人看来,以上乱象可视为“自由带来的弊病”,同时却又是“崇高事业难免生出的恶果”,诚如同为辉格党的洛克(其恩主为辉格党创始人沙夫茨伯里伯爵)在他的《政府论》(下篇)中所说,人生而自由,在自然状态下,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设立政府的目的正在于此——一旦财产和人身自由权利遭到剥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将不复存在。
然而,在土耳其,由于民众的自由惨遭剥夺,帝国的财富便轻而易举沦为少数人的专利。蒙太古夫人甫抵帝国首都,便惊叹其规模不下于欧洲名城巴黎或伦敦,然而当她步行至郊外,乃益发感到震惊:“君士坦丁堡周围的墓地比整个城市要大得多——如此大片土地在土耳其竟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耗损掉。有时候,我会见到延绵数英里的墓地,居然属于那极不显眼的村庄。这类村庄原先都是一些大城镇,可惜并未留下任何往日繁华的遗迹……地位特殊的家族坟墓,都用栅栏围起,并在四周栽种树木。而苏丹和一些大人物的墓中,还有永不熄灭的长明灯。”据说一盏灯的费用便远过于中等之家的岁入——苏丹们不仅生前穷奢极欲,死后也要享受特殊待遇。日后蒙太古夫人在报刊著文抨击英国政坛腐败现象,或正有感于此而发。在信末,蒙太古夫人不动声色地写道:“……因为这一任苏丹的统治可谓既血腥又贪婪,我倾向于相信人们皆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它的终结了。”
在抵达奥斯曼帝国之前,蒙太古夫人途经法国、德国以及荷兰等国,各地风俗、商贸以及政治、经济状况,在她笔下亦有生动体现。不过,出于党派观念和政治立场,她对西欧各国的态度也大相径庭。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国,与国内托利党暗中勾结,时刻准备复辟。而信奉国教的辉格党则视法国(和西班牙)为仇敌——在欧洲大陆,他们主张与同为新教的荷兰缔结战略同盟,共同抵御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王朝联手打造的新帝国。在辉格党人看来,与奉行绝对君主专制的法国相比,荷兰的共和制虽然未必合乎英国国情,但毕竟没有那么讨厌。
从里昂穿越大半个法国来到巴黎后,蒙太古夫人致信里奇夫人,描绘她在外省的见闻:“当驿站的马匹更换时,整个城镇都出来乞讨,他们的脸瘦得可怜,衣服又薄又破烂,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来表明他们处境的悲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黎的豪奢浮华——在枫丹白露的国王狩猎宫,国王和情妇以及贵族“拥有一千五百个房间,无不美轮美奂、富丽堂皇”。在蒙太古夫人眼里,法国贵族大多脑满肠肥,既傲慢自负,又颟顸无能——他们居然对一名英国通缉犯约翰·劳(John Law)毕恭毕敬——“他对此地的公爵(摄政王)和其他所有贵族都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而这些人对他却是无比地恭顺尊敬。真是可怜的家伙啊!我每一思及他们那卑贱的奴隶相,就想到巴黎市中心的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蒙太古夫人此处提及的约翰·劳是苏格兰经济学家、财政金融家,1716年,他在巴黎创办法国首家银行,率先发行纸币。次年,他为法国制定开发美洲法属领地路易斯安那的“密西西比计划”,但结果因过度投机而崩盘(几乎与之同时,英国人也炮制出“南海泡沫”,引发毁灭性股灾——蒙太古夫人损失惨重)。至于蒙太古夫人为何会联想到胜利广场,据考证,乃是由于广场上曾矗立一尊路易十四的雕像,雕像基座的各个角落都匍匐着卑微而勤勉的奴隶——堪称“太阳王”治下法国宫廷“臣仆”奴颜婢膝的真实写照。
和法国政体不同,十八世纪初的德意志境内邦国林立,犹如一盘散沙。在写给布里斯托尔夫人的一封信中,蒙太古夫人从辉格党视角出发,将令人震惊的贫富差距与政府形式联系在一起:两个相邻的城镇,一边是取得自治权的自由城邦,这里弥漫着商业和富裕生活的气息——街道修建整齐,人们穿着朴素,店铺商品琳琅满目,公共环境整洁卫生;另一边则隶属封建专制政府,所过之处,到处是年久失修的房屋,街道狭窄肮脏,路上居民稀少,其中约半数皆为乞丐。在蒙太古夫人看来,尽管两地同宗同源,但仅仅由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便造成如此巨大差异——政体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当蒙太古夫人抵达鹿特丹时,她似乎终于找到了理想社会的“原型”。在致马尔夫人信中,她描述当地的“商店和仓库整洁华丽,堆满数量惊人的优质商品,而且比我们在英国看到的便宜得多……这里的普通仆妇和女店主比我们大多数女士都干净得多,简直超乎想象”。除了发达的商业和贸易,蒙太古夫人对该地邮政服务的高效便捷印象尤为深刻。正如她在信中抱怨的那样,“在德国大部分地区,没有什么比邮政监管更为糟糕”;而在法国,她经常“迟迟未能收悉亲友书信”——巴黎警察总监以拦截和私拆邮件为消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据说这是法王授予这一职位的特权。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在共和制的荷兰,“书信往来就像发条一样顺利”。
与热衷于发动武装叛乱并寄望于外国武装干涉的托利党人不同,辉格党的宗旨是最大限度维护欧陆力量均衡,而英国可以趁机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和拓展殖民地。旅居巴黎期间,蒙太古夫人从当地友人口中得知,流亡的詹姆斯二世贼心不死,仍在招兵买马,蓄谋反攻英伦,效仿其父查理一世,再次发动内战,蒙太古夫人对此深恶痛绝。1716年,当她穿越尸横遍野的彼得格勒(Petrograd)战场,目睹交战双方的惨状时,禁不住给友人蒲柏写信,表达她对战争的厌恶和愤怒之情。后来,她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致威尔士亲王妃的一封信中善意地提醒,君主和他的人民是利益共同体:国王应当“以人民的幸福为己任”。回国以后,蒙太古夫人倡导预防天花接种术,得到英国王室大力支持,欧洲王室竞起效仿,传为现代医学史上一段佳话。
由于欧洲战乱频仍,身处颠沛流离之中,蒙太古夫人在《东方来信》中并未能尽情展露其党派及政治观念。根据英国文学批评家乔治·帕斯顿(George Paston)在《蒙太古夫人和她的时代》(1907年)一书——书中收录若干蒙太古夫人生前未发表(且未被销毁)的信件——中的看法,土耳其之行对蒙太古夫人意义重大:此行不仅增广了她的见闻,而且进一步坚定了她的辉格信念。在此后的书信、日记及政论文中,她念兹在兹的“执念”是警告其同胞“注意专制主义的危险,这种危险始终存在于一个至今仍然处于君主统治之下的国家——无论这种统治看起来多么仁慈”。事实上,这也是蒙太古夫人日后对以罗伯特·沃波尔为首的辉格党矢志不渝的根本原因:沃波尔在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长袖善舞,以捍卫英国人民自由为旗号,一面削弱贵族势力,一面架空国王权力,使得光荣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在英国深入人心。凡此种种,皆与蒙太古夫人的理念高度契合。
反对派在《工匠》(Craftsman)、《常识》(Common Sense)等刊物上著文抨击沃波尔。罪名之一是他通过贿赂议员全面掌控下院,而下院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进而侵犯到“贵族的权益和人民的自由”——蒙太古夫人的表弟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早年尝试以剧作家为职业,但因政治讽刺喜剧《帕斯昆》(Pasquin)遭当局查封,被迫转向小说创作,由此对专权的沃波尔及其政府恨之入骨。罪名之二,有人指责沃波尔缺乏原则立场,一味追求政治平衡术,所谓“革命和解”(Revolution Settlement)实际是一种“只为少数群体利益而运作的制度”。此外,更有人指控沃波尔组织涣散无力,纵容贪腐恶习,导致官场乱象丛生,世风日下,因此必须辞职谢罪。针对上述谰言,蒙太古夫人自告奋勇创办刊物《常识的胡言乱语》(The Nonsense of Common-Sense),奋起反击。她将还政于国王的论调斥为“无稽之谈”,更反对打着共和旗号的“暴民统治”——沃波尔被反对派讥为寡头政治的“巫师”,而蒙太古夫人则认为“这种寡头政治特别适合英国政府:它由那些由于经济实力强劲而有闲暇去寻求启蒙、能够欣赏并捍卫自由理念的人所组成”,这些政治精英既要保护那些愚昧无知、不明真相的民众利益不受侵害,又要防范那些自诩“天命在身”的国王作出鲁莽和疯狂之举。
在未刊稿《制止腐败恶习蔓延的权宜之计》(“An Expedient to put a stop to the spreading Vice of Corruption”)中,蒙太古夫人一方面承认沃波尔政府对于惩治贪腐不力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一方面更竭力驳斥反对派提出的整治举措——“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种恶习的蔓延呢?难道要取消议会……恢复绝对王权(Arbitrary power)?”她所提出的老辉格派(old Whiggish)方案,是通过“权利对于权力”的制衡(洛克语),迫使权力运行机制大白于天下,从而让贪腐无处遁形。正如十九世纪辉格党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言,人们应该去“质疑权力,而不是质疑恶习”——按照这一评判标准,对于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以及奥斯曼苏丹而言,纵情声色之类恶习只能算是“小节有亏”,与之相比,他们企图恢复绝对君主专制的妄念才更值得世人警惕。
转载请注明来自亚星官方网-亚星开户-亚星代理,本文标题:《杨靖︱《东方来信》背后的辉格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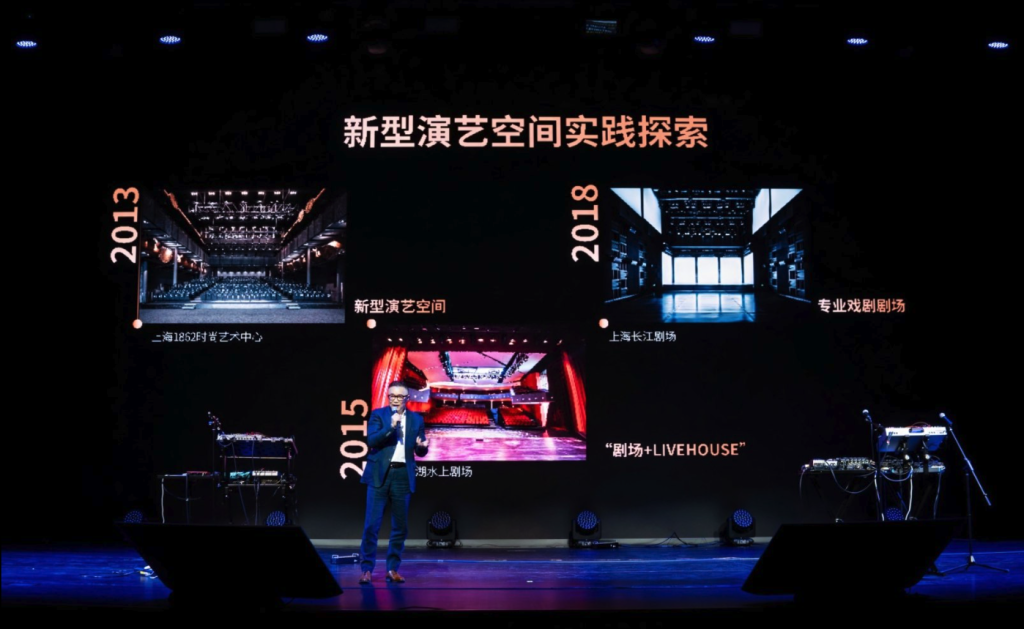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