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4年,大宋庆历四年,大辽重熙十三年。
这个年头,挺有意思的。掐指一算,距离北宋960年建立,已经过去了84年。抬头一看,距离北宋1127年灭亡,也是剩84年。所以,今年算是北宋历史的中间点。
但是这一年之所以有名,还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庆历四年”这个词。“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开头第一句,咱上学的时候都背过啊,这个年头就这样印在了每个中国人脑子里。所以我们《文明之旅》讲到了这一年,咱也没得选,只能讲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

我们多次讲到范仲淹。从寒窗苦读到考中进士,从地方官到京朝官,从经略边疆的儒将,到主持改革的宰相,我们真是看着他一步步长大的。范仲淹伟大吗?伟大。但是把他这辈子做的事情拉出清单来,好像也就那么回事:要说苦孩子逆袭成功,中国从底层出身拼出来的人物,那是车载斗量;要说为政一方造福百姓,那中国历史上这种好官儿多了去了;要说上战场为国征战,宋朝是前有狄青、后有岳飞,最后还有个文天祥,范仲淹的军功并不突出;要讲政治改革,咱们上一期节目都说了,庆历新政是失败的。无论是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后世的政治遗产,它跟20多年后的王安石改革没法比。
你看,这么一捋,范仲淹好像也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古今中外的人对范仲淹的评价又是出奇地高。
比如,南宋的大学者朱熹就说,范仲淹有一项大功劳,什么呀?我朝士大夫的精神为之一振啊。比朱熹晚大概一百年,南宋学者吕中说得就更狠:我大宋朝排名第一的人物是谁?范仲淹啊。这是宋朝人对他的评价,还有北边的金朝人呢?——金朝跟宋朝可是敌对关系啊——金朝大学者元好问,他说,像范仲淹这样的人物,一二百年不见得有一个。你听听,已经不是宋朝第一了,是几百年间的天下第一。到了明朝,思想家李贽说,宋朝虽然亡了,但是范仲淹没有亡啊。这就有点说他永垂不朽的意思了。那当代学者的评论呢?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就说,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把范仲淹当典范,这是一个共识。
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了?中国人讲立功、立德、立言,范仲淹的确是都做到了,但是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这些成就,至于让后人对他评价这么高吗?什么本朝第一,什么百年一见,永垂不朽?
好,那就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穿越回公元1044年,来看看范仲淹到底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什么转变?也重新来读一读这篇《岳阳楼记》,看看它又是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文明回响千年的黄钟大吕。

儒家的缺陷
范仲淹当然很了不起,但是一个人如果获得了那么高的评价,那肯定不是因为他对当时当世所作的贡献,而是因为他在文明的关键转折点上的关键作用。就像有人评价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听听这个话,孔子的地位,哪是他老人家活着的那73年能衡量的?衡量的标尺不说是万古吧,至少也得是整个中华文明史。

好,那如果换一个标尺来评价范仲淹的话,这根新尺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到整个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去找了。
儒家是什么?我们脑子里会出现一大堆的联想词,可能是“仁义道德、四书五经、士大夫”,也可能是“虚伪保守、愚忠愚孝、老顽固”。但是请注意,这是我们这代人从后往前看,两千多年的儒家的身影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每个时代,儒家的面貌其实都不太一样。再深想一层,我们这代人看儒家这个词,就像端详一个博物馆里的展品,老想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因为它定型了,不再演化了嘛。而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那儿,儒家是从周公孔子流到他们眼前的一条河流,他们是会往这条河流里面加入新东西的。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儒家?儒家是每一代士大夫用思想和行动不断创造出来的,是日新月异的。

最早的儒家什么样?这个问题,在当年的民国学术界还引起过一场大争论。像章太炎、胡适、傅斯年、冯友兰、钱穆,都有各自的观点。总体上不过是几种结论,要么说“儒”是一种职业,在民间主持各种婚丧嫁娶的仪式的;也有说,“儒”就是老师,是传授知识的;也有说,“儒”是一种官职,是负责音乐历史之类文化活动的。
咱们不陷入学术争论,咱们就找点感性认识,你看汉代的许慎那本《说文解字》,上面说“儒”是什么?一个字,“柔”啊。两个字,“术士”啊。说白了,那个时代大家对儒的印象,恐怕就是远远一看,一个柔柔弱弱,走路斯斯文文的,穿得宽袍大袖的人,就知道这个人的肚子里有很多学问,什么学问?不是怎么种田、怎么做工,而是各种各样的礼仪规矩,那这个人就是“儒”。
至于他具体干什么,那就得看雇他们干活的东家是谁了。民间要办婚丧嫁娶祭祀仪式的,怕自己坏了规矩,要请儒来操办,跟今天需要婚礼司仪是一样的;国家需要继承前代的规矩礼仪,也是怕坏了传承,要请儒来做官;当时社会的知识总量很小,主要的知识,就是各种礼仪,所以要请儒来当老师。
但是你发现没有,不管儒具体干什么,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有东家的人。用今天的话说,都是靠甲方订单吃饭的乙方。
儒家这种靠着东家吃饭的形象,在民间是有刻板印象的。当时不喜欢儒家的人,比如墨家,就嘲笑他们,说每当富人家里有丧事的时候,儒家就最开心了,奔走相告,“买卖终于上门了!这回可以吃上饭了。”
我们今天提到儒家,都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主张,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儒家总体上其实就是工具人,就看甲方是不是用得着。
比如,汉高祖刘邦,刚开始是一百个看不上儒家,拿着儒生的帽子往里撒尿。他为啥这么傲慢?因为他觉得儒生讲的仁义道德那一套,打不了天下嘛。甲方觉得他们没用,就把订单取消了嘛。但后来刘邦又为什么重用儒生?有一个故事——
刘邦刚立国的时候,手下大臣们跟他都不见外,打交道的时候很松弛。松弛到什么程度呢?大臣们经常在大殿上喝醉了酒,拔出剑来就砍大殿的柱子。这么没大没小的,刘邦就不高兴。那怎么办呢?其实解决方案是现成的,人才也是现成的,就是重新启用儒家啊。有人就跟刘邦说,哎,我们儒家打天下是不行,但是守天下我们拿手啊。要不我帮你找找山东的儒生,帮你制定一套上朝的礼仪,保管你满意。这个工程不小,搞了两年,终于制定了整套上朝的礼仪,谁先谁后,几点几分,什么角色怎么行动,全都有规矩,这一大套整下来,群臣一个敢乱说乱动的都没有。把刘邦爽的啊,“今天我才晓得了,晓得做皇帝的那种尊贵的滋味哦”。
你可以咂摸一下这个故事的意味,对于儒家,侮辱也好,重用也罢,在刘邦这个甲方那里,你都是个工具,在该用你的地方用你而已,谈不上什么尊崇。有人可能会说,那到了汉武帝时期,不是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儒家的地位不就上去了吗?其实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有质疑。咱们不管学术争论,只看一点就行:皇帝甲方们非常清楚,统治国家这个事,是不可能只用儒家的。从汉朝到清朝,只要是有皇帝的时候,都是所谓的“外儒内法”,即使口头上再尊崇儒家,那也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态度而已。汉宣帝有一次对太子恨铁不成钢,一着急,就把真话说出来了:我们汉家的制度,既要用王道也要用霸道,是杂着用的,哪能死心眼只用儒家呢?
其实,这也不是皇帝一家的看法。比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把当时的主要学派都评点了一遍,他评论儒家:儒家的学问很大,但是不得要领,忙活半天,都没啥用。所以,你要干事,别什么都听儒家的。但是有一条,如果你要维持社会秩序,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那一套,儒家还是管用,作用不可替代。
你看,儒家虽然传统深厚,但是西汉的儒家,恐怕很难说是一种独立的精神信仰,它就是一门手艺,一种能力,有用,但是不解决全部问题;有社会角色,但是这个角色严重依附在甲方,也就是皇权的身上。
表面看,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一句话你可能知道,叫“干活不随东,累死也无功”。如果甲方的需求突破伦常道德底线呢?儒家这么浓烈的乙方气质,它的行动就可能也随之突破底线了。比如说,谶纬,也是汉朝的时候最兴盛。所谓谶纬,你可以理解成附会在儒家学说上的各种迷信。比如,王莽要篡位当皇帝,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搞各种符命、祥瑞、谶纬。用迷信造谣,说老天爷让他当皇帝。大家要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张向荣老师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里面的很多迷信,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甚至就是当时的大儒编造出来的。读这本书,我请你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不仅王莽,连推翻王莽的刘秀也是接着搞谶纬的。
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刘秀要搞谶纬迷信,就找到一个当时的大儒尹敏,帮他校订这些迷信书。尹敏就劝刘秀,说这些谶纬之书啊,又不是圣人写的,里面又有很多鄙俗的东西,还是不要搞了吧?刘秀不干,非要搞。尹敏说行吧,那我就帮你搞。最后把这批书送上去的时候,刘秀一看,里面有这么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君子的君字没有口,这不就是你尹敏姓的这个尹吗?为汉辅,不就是说你要当宰相吗?刘秀把他叫来问话,尹敏就坦白说,对啊,你既然信这一套,大家也都利用这一套编书,万一我添上这一句,你真让我当了宰相呢?这就是当时某些儒家的道德水准。
你可能会说,古人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可能确实也无法分辨什么是胡说八道吧?错了。分辨这种胡说八道,朴素的常识就够了。孔子当年就说,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嘛。东汉的王充,就专门跟这种胡说八道抬杠。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说法,某天洗头人就好看,某天洗头人就白头。王充就说,试试不就行了?你找个丑人在某天洗,看看是不是变好看了,再找个年轻人在某天洗,看他是不是白头了,不就行了。这跟今天的那个迷信,说二月二前剃头死舅舅,一样的,一对照就知道是胡说。而当时的各种儒生也跟着起哄,那肯定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就像那位尹敏一样,背后是有个人的功名利禄的目的。整个社会在这种风气中,是很容易沉沦下去的。
你看,这就是当时儒家的一个重大的缺陷,跟着甲方的指挥棒转,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是有可能堕落到没有底线的程度的。
本来,儒家作为皇权的一个工具,就这么混下去也行。但是不好意思,到了东汉后期,它突然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本来班里就一个学霸,突然转来一个外地学霸,混,也混不下去了。对,就是佛教,儒家要面对佛教的竞争了。

儒家的困境
刚才讲到,儒家在东汉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佛教。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迅速就野火燎原,歘地一下就普及开了。佛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很多人对佛教有误解,以为佛教也是凭着各种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的神话来开拓市场的。在民间社会,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可能也知道,佛教其实是一种无神教,没有什么神仙鬼怪,什么是佛?佛的本义是觉悟者。人人都能通过某种方法,能达到那种状态,一个坏人还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佛教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上层有知识的人的魅力在于:它回答了两个儒家不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可观察的世界之外,宇宙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所谓的宇宙观,传统儒家学说里是没有的,所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嘛。但是这一点,佛教里有,所谓“三千大千世界”什么样,佛教说得是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儒家什么时候才有宇宙观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阶段,也是和佛教竞争的结果。
你看,这一年是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有一个官员叫周敦颐,就是我们语文课上学过的《爱莲说》的作者,被调到了南安军,今天的江西大余县工作。就在这里,他收了两个学生,谁啊?程颐和程颢,也就是著名的明道先生和伊川先生。这三个人的相遇,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其中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太极图。这就是儒家提出的宇宙论的模型。这是后话,我们将来再说。
比宇宙论的问题更要命的是人生论问题。儒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也不回答,那就是:在人的生死之外,那些彼岸的、超越性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传统儒家不讨论。有学生是问过孔子的,鬼是什么样。孔子说,怎么对待活人还搞不清楚呢,哪知道怎么对待鬼。又有人问,那死之后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活得还不明白呢,哪知道什么是死。
孔子的态度很实事求是。但问题是,这是一个人最根本的疑问啊:我死了之后怎么样?人究竟有没有魂灵?这是连祥林嫂都要追着问的问题啊。一个人想要过好,光有物质资源是不行的,他必须得寻找意义。意义在哪里呢?一定不在人生看得见的此岸,一定是在超越性的彼岸,在无尽的时空中。所谓something bigger than myself,那些比我大的东西。这就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嘛,“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
那既然儒家不回答这个问题,佛教就来回答,什么六道轮回啊之类的。不管人家的答案好不好,至少人家佛教有啊。在这一局的比赛上,儒家丢分丢得太多了。
我举两个例子,你感受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欧阳修。现在是庆历四年,到下一年,他就要写出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了。欧阳修是一个标准的大儒,他开始并不信佛,甚至主动写文章驳斥佛教。但是,就从这几年开始,一方面当然是政坛失意,另一方面,是岁数越来越大,就越开始追问一些关于生死的问题。当时,谁能跟他讨论这些问题呢?只能找高僧。到了晚年,欧阳修的高僧朋友越来越多,对佛教的信仰也越来越深。据说,欧阳修临终前几天,派人到附近的寺庙去借了一本《华严经》,读到第八卷的时候,才溘然长逝。我们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知道欧阳修又叫“六一居士”,所谓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嘛,这是他晚年才给自己起的号。连欧阳修那样的儒家学养,那样的精神境界,最后也走到这一步,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教对超越性问题的回答,补上了一个重大的空白,太有魅力了。
另一个例子,是我前不久去洛阳看龙门石窟。龙门研究院的高丹老师指给我看,一个非常小的佛教洞窟,上面有题记,也就是造这个石窟的功德主留给后人的一段话,字迹漫漶,很难辨认,读下来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说我的妻子死了,我自己眼睛也瞎了,我也没有儿子,还重病缠身,眼看就活不了了,我这辈子就像蜉蝣一样,短暂得很。但是,我也可以花钱在这龙门的山上挖一个小洞,造一个佛像,我为了能永恒而存在啊。
我请你切身体察一下,这个可怜人,生活在唐高宗总章二年,那个时代大人物很多,而他呢,渺小得什么都不是。他的生命马上就到尽头,亲人也都没有了,所有现实世界的东西对他都没有意义了,他还能追求什么呢?其实就是人间最有魔力的两个字:永恒啊。而在当时,只有佛教能给他这种心灵的安慰。儒家是无能为力的。
有人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很有意思。把一个人扔到孤岛上,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穆斯林或者佛教徒,他们都还是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和他们心中的终极信仰沟通。但是,如果把一个儒家士大夫流放到了孤岛上,那他还是一个儒家吗?麻烦了,儒家的所有信条都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有处理的准则,但这里是孤岛啊,只有他一个人,那他怎么还能是儒家呢?
儒家即使处理死的问题,在意的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汉语中有一个死的代名词叫“寿终正寝”,什么意思?古时候的诸侯、士大夫,要死也得死在正房里,也就是平时办事的大厅里,不能死在旁边的小卧室里。为啥?因为小卧室,那没准就是哪个小妾的地方,死在那儿,容易让小妾们在大人物临死的时候干涉朝政或者继承人的人选。你看看,儒家聊死的话题,着眼点还是活人之间的关系。
你看,儒家把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一个精神阵地,拱手让给了佛教啊。
还不仅如此,佛教因为拿到了彼岸世界的解释权,还打开了精神世界的向上提升的空间。
就拿整个唐朝来说,我们至今还在仰望他的精神世界的人,都有谁?要论帝王的雄才大略,那是唐太宗;要论诗情文采,那是李白杜甫;但是要论人格伟大,我们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应该是玄奘法师,唐僧啊,他西天取经、不畏艰难的精神,激励了多少中国人啊。你看,又是佛教得分,儒家丢分。
说了这么多儒家的问题,不是为了批评儒家,只是想为你勾勒一个历史发展的粗略轮廓,从东汉到隋唐,儒家确实有一个低落的时期。
但是,到了宋朝,儒家开始绝地反击,有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更新。而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就是这次自我更新的里程碑。

儒家的复兴
兜兜转转这么久,我们终于要说到范仲淹和《岳阳楼记》了。范仲淹这辈子的很多做为,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有一些零散的介绍。那总括起来,他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呢?
欧阳修评价范仲淹,说他什么事都要管,做事从来不挑三拣四、趋利避害。南宋时候的朱熹也说类似的话,说他,“无一事不理会过”,所有的事都认真,都担在自己身上。这是一种什么行动做派?还是朱熹一句话总结得好,他说这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的事,都是我的事。确实,这也符合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面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好,我就高兴,天下不好,我就发愁。
今天的人,听到这几句话的评价,可能没什么感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什么“先忧后乐”,都是耳熟能详的褒义词,有什么呢?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不都这样吗?
不一样。我们今天听熟了不觉得振聋发聩,但回到《岳阳楼记》的时代,之前的人可从没听过这句话,是范仲淹第一次把它精确地表达了出来。从儒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出现这句话,其实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你看这句话里面,强调的这对关系,这边是我,那边是天下,中间什么都没有,是我这个人和那么大的天下之间的直接关系。
你意识到什么没有?刚才我们讲的儒家的那几个缺陷,一下子就被这句话给补上了。
首先,原来儒家是有东家、有甲方才能行动的,现在不用了。我和天下的关系,是我自己认定的,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活是我主动承担的,谁也不用来雇我,谁也开除不了我。至于原来儒家的雇主,皇帝,在我这个逻辑里啊:《岳阳楼记》里面不是还有两句吗?“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都关心,都负责。皇帝不再是我一个士大夫和天下之间的中间商了。我绕过皇帝,对天下的事情负责。
再来。刚才我们说,和佛教相比,儒家的超越性不够,只关注此岸的事,人间的事。但是现在有了这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那就全部补齐了。
往上看,天下是什么?天下指的可不是什么具体的领域,你能想到的所有范畴,人民、土地、悲欢,都是我要负责的对象。这一下子把一个士大夫要负责的范围扩展到无边无沿的境界。儒家在历史上有类似的提法,比如,先秦的时候儒家讲,以仁义道德为己任;东汉的时候,儒家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你听出区别没有,这都是说,我要看住这一小块地方,仁义道德,或者是精神风貌,替谁看?不还是替帝王看住吗?说到底,还是一种乙方心态。
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直接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承担终极的责任,超越性就够了。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思想实验吗?一个儒家士大夫被扔到了孤岛上,他现在想的,不是什么婚丧嫁娶的礼仪,不是什么父子君臣的秩序,他心里想的是天下,这不就和基督徒、佛教徒一样了吗?都有一种终极的精神支撑。

我们再深入地想,儒家还有什么弱点被补上了?那就是关于自我的安顿。
在早先的时候,儒家安顿人的方式,就是找到合适的和他人相处的模式。怎么相处?靠礼仪。你想,礼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不管你内心怎么想,你只要这么做,就算是完成规范了。虽然礼仪的源头,是人的情感,但是,礼仪的规范越严格,对于内心情感的要求就越不高。父母去世,你守孝三年,就算是孝子了。至于你是不是真的内心悲痛,那就管不着了。
但是你看范仲淹这句话,先忧后乐,天下好不好,是要落实在你的感情世界里的。不是搞个什么仪式,做个什么动作,就完事的。你要拿出自己当下的、真实的情感,实实在在的忧愁,真真切切的欢乐,来对应天下的好坏。你不是做给谁看的,你就是通过这种忧乐的情感体验,让自己的人格不断攀援向上。
这一来就解决了儒家的一个大问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如果不得志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你看孔孟的答案仅仅止步于,你就待着吧,管好自己,当个隐士就行。但是,范仲淹提的要求明显要高一大截,那不行啊,天下有道无道,自己是穷是通,这都是外在环境的变化,都不能耽误我在情感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记得《岳阳楼记》里面还有一句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的情感不是跟着眼前的得失、身边的事情波动的,我的情感是对整个天下兴亡的响应。这就对一个士大夫在困境和挫折的时候,提出了人格上的要求。

你看,我们刚才分析了三个方面,儒家的缺陷都被补上了。儒家再也不只是皇权的附庸了,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精神世界;儒家再也不是只管仁义道德的说教了,它把自己责任扩展到无限大,大到要用天下来形容;儒家再也不是只看外在行为的礼仪专家了,它的道德要求一直向人心深处抵进,直达忧乐,直达人的情感底层。
我们这里这么强调范仲淹的这句话,不是说,这都要归功于这个人和这篇文,而是说,儒家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跌宕起伏,由衰转兴,就是在这个阶段。而它的标志,就是范仲淹这一生的人格实践和《岳阳楼记》这篇雄文。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回过头去致敬孔子。因为孔子在儒家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意义。
孔子当年,也是多少摆脱了对东家、甲方的依赖。孔子在历史上有一个名头,叫“至圣先师”,他是不是至圣,可以争论,但他确实是第一个老师,通过自己办学校、收学费,通过那个时代的知识付费,养活自己。不要小看这件事,同样道理,贝多芬就是因为可以通过出版乐谱养活自己,不用再讨好什么公爵伯爵,他才会成为一代自由主义音乐大师,他的音乐才能摆脱宫廷娱乐的定位,成为经典的、凝神贯注的严肃艺术。孔子也是,正因为他这一生,不只是把自己当成是某个君主的雇员,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乙方,他才会有那么独立而伟大的人格,他才敢说什么“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更重要的是,孔子也是在儒家的传统中,最早强调超越性的。他反复提到的那些词:比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再比如,“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都是超越性的词。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经常当口头禅念叨的那个词:“君子”。
孔子讲过一句很令人费解的话,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上半句好理解,君子嘛,怀里要抱着德性。但这下半句是啥意思?小人怀土?和君子对应的小人,怀里就抱着土?
后来看朱熹的《四书集注》注释才明白了,所谓“德”,就是一种本应如此的、抽象的、超越的善。而“土”呢,就是指一个人沉溺在自己的环境中,被周边的环境因素深深地制约,这叫“土”。对啊,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土”,其实也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被自己的环境深度影响,难以自拔,不能超越性地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
你看,把“土”和“德”一对立,我们突然也就明白了“德”的意思。它不只是讲仁义道德,它其实是一种超越性的要求。你要是有德,那你的那个德,就是凌驾于一切环境因素之上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看情况,不能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立场,你的标准应该是立于天地之间的永恒的标准。心里有这个行事准则的人,才是君子。
你看,孔子在先秦时代就提出来的这些创造性的观念,经历了扭曲,经历了衰落,但是,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年头,借由范仲淹这个人,借由《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再一次振作了起来。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朱熹对于范仲淹表扬,它也成了宋代士大夫对自身社会角色的一种自觉。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大门。
最后,还是要多说两句《岳阳楼记》。这篇文章里,还藏着两个冷知识。
第一个冷知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个滕子京是谁啊?是范仲淹的一个朋友,他为什么被贬谪到巴陵郡啊?因为他做官离任审计的时候,有人汇报16万缗的公款去向不明。朝廷想要继续调查,滕子京居然把相关的账目,一把火给烧了,是因为这个事被贬谪的。这件事的真相扑朔迷离,范仲淹也一直在替滕子京解释、喊冤,说根本没有那么多,但是毕竟,滕子京留在历史上的背影是“疑似贪污犯”。
第二个冷知识,《岳阳楼记》里面有一段,“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我看整个巴陵的景观啊,就是洞庭湖最好,后面又是一段活灵活现的描写:“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但你知道吗?范仲淹其实压根儿就没去过岳阳楼。他只是看了滕子京给他画的一幅画,然后就一挥而就写了这篇文章。不算是山水游记,算是看图说话吧。

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两个冷知识之后,对《岳阳楼记》的评价会不会降低?而这正是我今天最想说的:精神世界的超越性,是不被环境、载体所限制的,一篇千古雄文怎么会被这两个小瑕疵掩去了光芒?那几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几句话是远远超越于这篇文章,超越滕子京这个人,超越创作过程中的存在了。
它早就拔地而起,直冲九霄,和天地精神独往来,虽万古而不磨灭了。只要是听得懂中文的人,不管身在何处,心有何属,听到这几句,必然是心头一暖,精神一震。
这就是1044年,庆历四年,我为你讲的范仲淹和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1045年,再见。

致敬
本节目的最后,还说啥呢,必须致敬范仲淹和《岳阳楼记》啊。致敬的方式,就是把368字的千古名篇,给你念一遍。你也怀怀旧,我也过过瘾。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2025年的第一天),致敬范仲淹,致敬中华文明史上所有的君子,他们,像漫天的星斗,像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像未来人们凝视咱们的眼睛。
参考文献
(宋)范仲淹撰,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中华书局,2020年。
(宋)周煇:《清波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撰:《辽史》,中华书局,2013年。
程应镠:《范仲淹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
王启玮:《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刑爽:《忧乐圆融:北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
王炎平:《科举与士林风气》,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阎步克:《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汤勤福主编:《中华礼制变迁史》,中华书局,2022年。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中华书局,2022年。
陆敏珍:《宋代家礼》,中华书局,2022年。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西书局,2019年。
叶国良:《中国传统生命礼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
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吴飞:《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余秋雨:《君子之道》,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
(日)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诸葛忆兵:《范仲淹传》,中华书局,2012年。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共1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耿战超:《〈论语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林鹄:《政治史的魅力:结构、事件与担纲者》,《学术界》,2023年第11期。
杨光:《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梅莉、宋相阳:《从传说中的阅军楼到中国文化地标——岳阳楼之声名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仝相卿:《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理念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
郭炳洁:《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李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背后》,《历史教学》,2011年第22期。
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李伟国:《范仲淹〈岳阳楼记〉事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转载请注明来自亚星官方网-亚星开户-亚星代理,本文标题:《公元1044年:《岳阳楼记》为什么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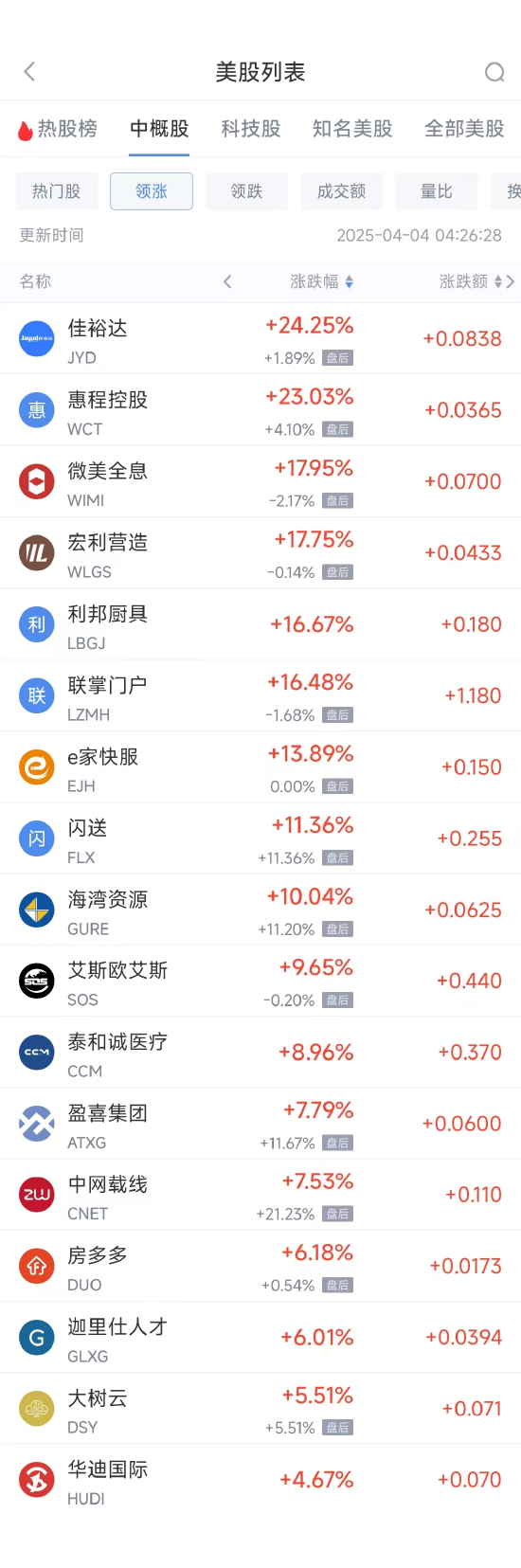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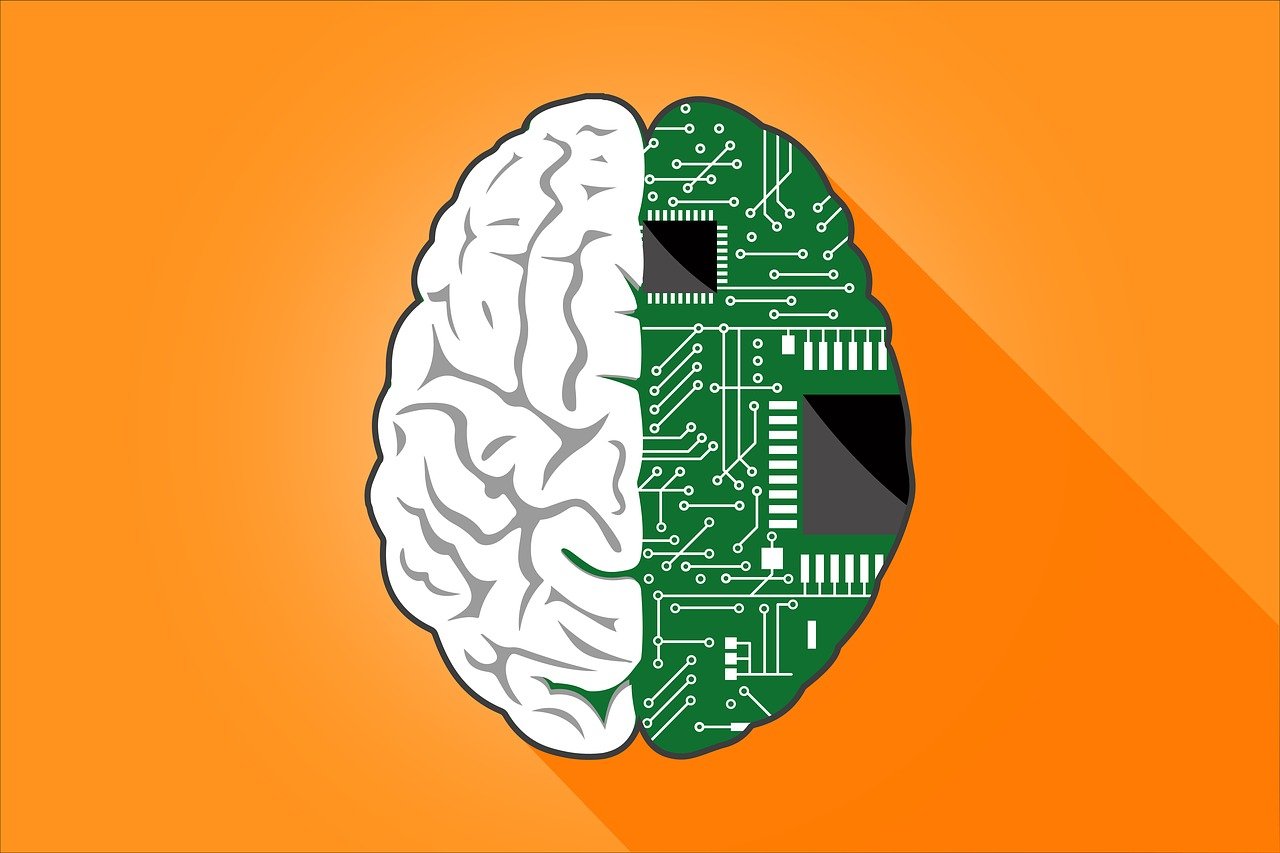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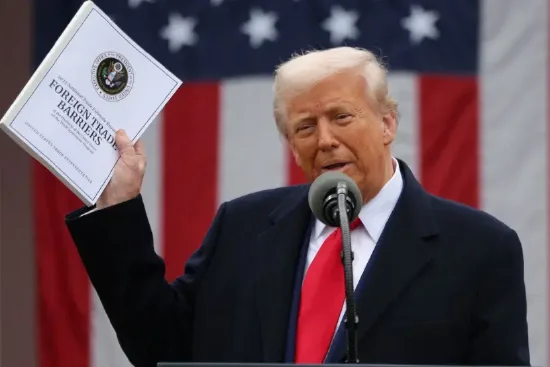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